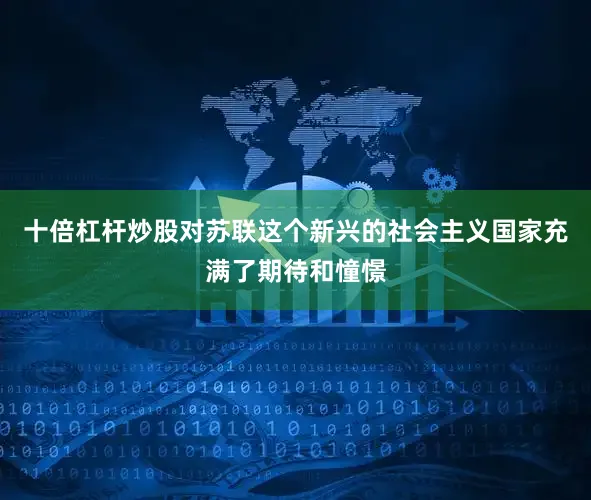
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许多中国人都纷纷前往苏联进行考察,甚至蒋介石也对苏联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高度赞赏。然而,徐志摩的苏联之行却并非如他所期待的那般愉快,反而让他看到了一个失去了光彩、变得苍白丑陋的苏联。
1925年3月,徐志摩途经苏联,并访问了多个地方和人物,之后他写下了《欧游漫录》,详细记录了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感。刚开始,徐志摩与大多数中国青年一样,对苏联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充满了期待和憧憬。但很快,他就被眼前的现实所打击,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。
“随着我进入苏联的深处,我渐渐看到了人民的困苦。今天,我站在赤塔车站,看见许多褴褛的孩子,年龄从三四岁到五六岁不等,他们站在月台上向乘客讨要施舍,而不是以一种谦恭的态度,而是那种似乎手伸出来就绝不允许空着的眼神。他们不只是出现在车站,连车站的餐馆里也可以看到无数的男女,衣衫褴褛,他们似乎什么都不做,只是用死寂的眼神凝视着你面前的热汤和面包。他们的脸色并不凶狠,但显得十分阴沉,令人无法不产生疑问,苏联人民是否还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然和喜悦的笑容?”
展开剩余78%在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后,徐志摩的失望情绪愈加强烈,他写道:“这里没有曾经的辉煌遗迹,只有被血染过的历史痕迹;这里没有光鲜的景象,只有破败的教堂;这里没有温暖的阳光,只有泥泞的街道;这里没有人性的喜悦,只有沉重的恐怖,黑暗,残酷的虚无。莫斯科,你集中展现了你破坏天才的所有威力,一只手拿着火种,另一只手握着杀戮的刀,完成你的任务吧,让千年后的子孙来这里朝拜,纪念你的不朽!”徐志摩眼中的苏联,仿佛已经失去了它曾经的文化和美好。
在此之前,徐志摩对苏俄的印象相当正面,尤其是通过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屠格涅夫等伟大作家的作品,他对俄国充满了理想化的向往。然而,当他亲身来到苏联时,他感到这一切似乎完全改变了。“在这场革命的火海中,最早被烧掉的是俄国的过去,那些专制、贵族、奢华、堕落的旧社会,那些穿着长裙的贵妇人,驾着镶金马车的贵族,递烟斗的朝臣,以及身穿猎装的贵族子弟,都已消失殆尽。曾经在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小说中出现的俄国社会全然消失,俄罗斯的文化也已荡然无存。”
为了更深入了解苏联的现状,徐志摩特地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,老太太告诉他,现在苏联已禁止销售托尔斯泰的书籍,屠格涅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也已无法购买。当徐志摩询问莫斯科还有哪些著名文学家时,老太太失望地回答:“他们都跑了,剩下的根本不值得一提。”
徐志摩还访问了一个著名的墓地,那里安葬了许多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人物。然而,这些墓地大多数都遭到破坏。当他来到契诃夫的墓前,心情极为复杂,写道:“今天的俄国,今天的世界,如果他看到了这一切,是否还能微笑?”
更让徐志摩惊讶的是,苏联的教授们生活的极为困窘。他曾拜访过几位大学教授,原本应当拥有优越生活的他们,居住的地方狭小简陋,衣衫破旧,甚至连头发胡须都多年未曾修理。看上去就像街头的流浪汉,远没有他想象中的风范。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原本社会地位不高的服务员,却表现出一种极端高傲的态度。徐志摩在乘坐火车时遇到了一位乘务员,感觉她不像是来为乘客服务的,而是来管理乘客的。她总是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态,讲话的语气很大,仿佛是在发号施令。如果有哪位乘客表现出不满,她立刻会加以训斥。
在徐志摩的眼中,苏联就像一个完全颠倒的世界。曾经令他向往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,他所看到的,是一片失落与黑暗。1925年秋天,徐志摩担任《晨报副刊》的主编,发起了一场“苏俄仇友”的讨论,激起了广泛的反响,甚至连陈毅也参与了这场辩论。
1926年1月,年仅25岁的陈毅写了一篇《纪念列宁》,并寄给了《晨报副刊》,文章中提到:“徐先生不该责备共产党人铁的心肠和铁的手段,您不妨看看帝国主义和军阀们手中的武器,看看他们如何凭借贫苦的工农作为主力军推翻旧世界。列宁正是利用这一点,运用自己的天赋和马克思主义理论,创造了工人和农民联合的革命,正是这些奴隶翻身了。”
然而,徐志摩对陈毅的文章并不认同,他认为陈毅只是在盲目地崇拜一种不完全可靠的学理,并幻想着革命的美好背景。
事实上,徐志摩的根本问题在于,他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庭,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,接触的多是上层社会的名流,与贫苦大众的生活完全无关。他以为世界应当是他所熟悉的那样,这也使得他在面对苏联的真实面貌时,自然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心理。
从《欧游漫录》中的描述来看,徐志摩眼中的“俄国文化”,便是贵族的奢华与淫靡,是旧秩序的象征。他无法忍受这一切的消失,因为那是他熟知的世界。说到底,徐志摩不过是一个身处上层社会、生活奢靡的花花公子罢了。
发布于:天津市牛策略-正规实盘配资平台-配资专业股票配资门户-云南炒股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